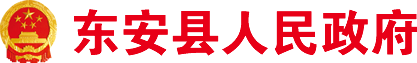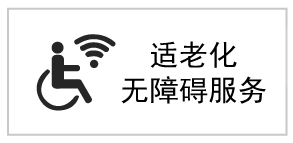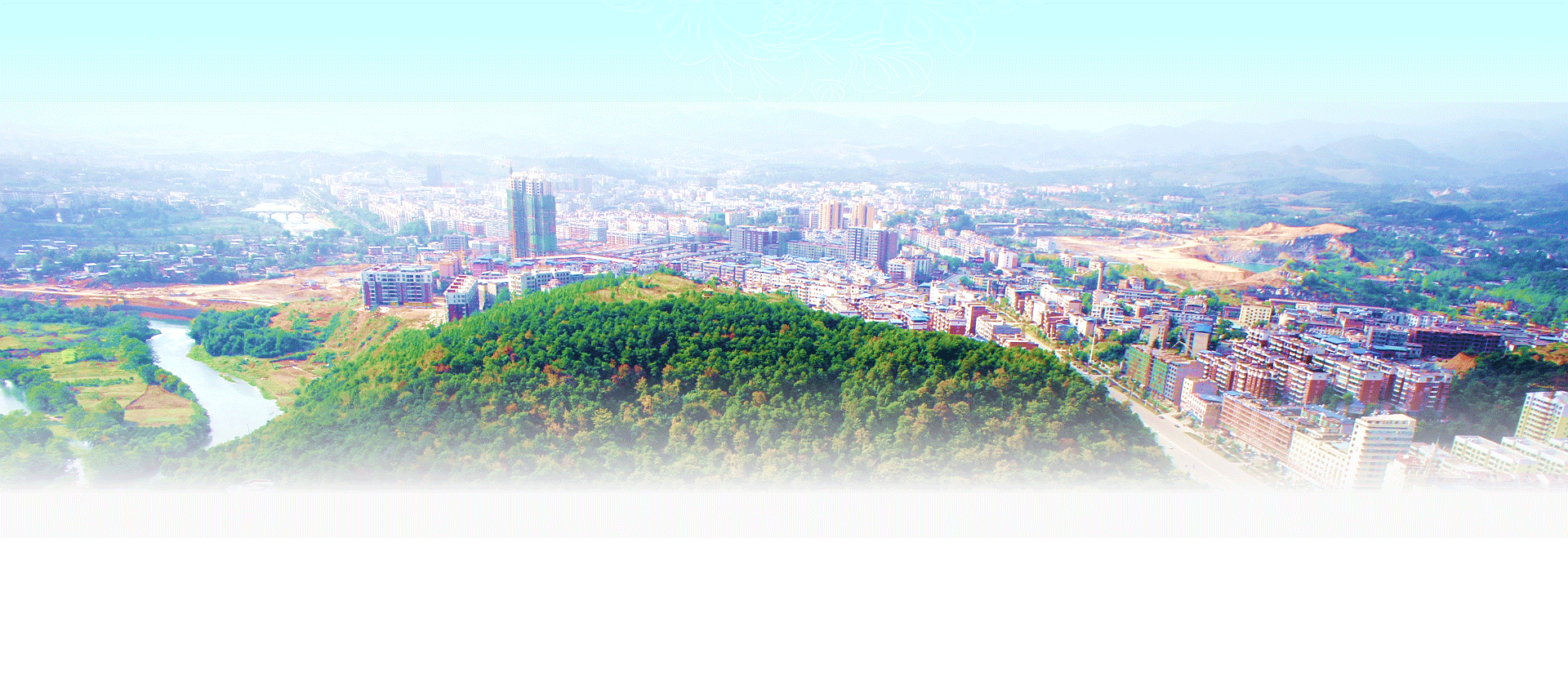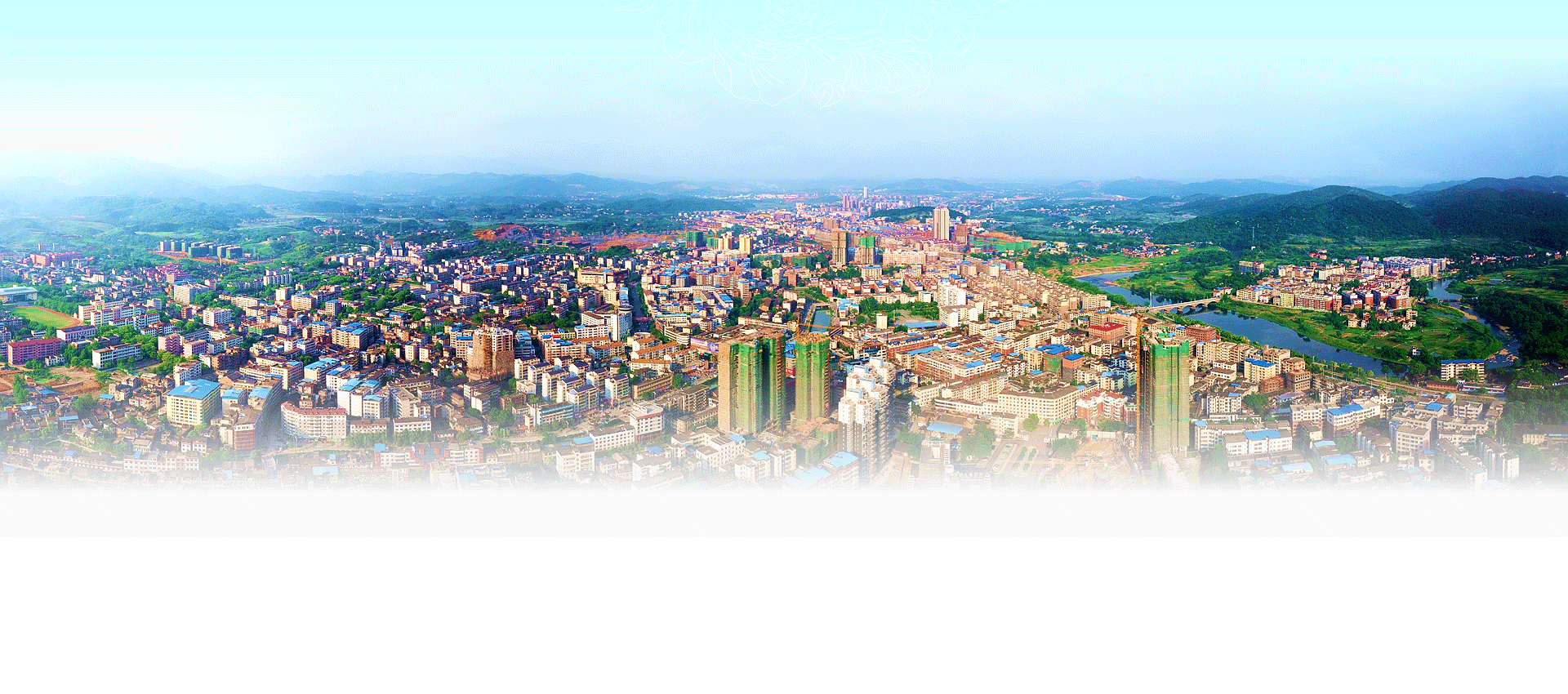發(fā)揮司法能動作用
懲治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
代海軍
刑事制裁在有效懲治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維護公共安全秩序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刑法條文本身所具有的概括與原則的特點,,客觀上影響了制度功能的發(fā)揮。為緩和立法的抽象性與司法實踐的具體性之間的矛盾,,近日,,“兩高”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辦理危害生產(chǎn)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同時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為司法機關統(tǒng)一適用法律審理案件提供明確指引,。
本次發(fā)布的《解釋》及6起典型案例主要圍繞《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的強令、組織他人違章冒險作業(yè)罪(《刑法》第134條第2款),,危險作業(yè)罪(《刑法》第134條之一),,以及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刑法》第229條)等4個罪名展開。從公布的內(nèi)容上看,,呈現(xiàn)出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是突出安全生產(chǎn)預防為主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安全生產(chǎn)領域逐漸塑型出以“安全預防控制”為主要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缎谭ㄐ拚福ㄊ唬穼ξkU作業(yè)罪的設立,體現(xiàn)了我國刑事立法從事后制裁向積極預防的功能轉向,,符合“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的總體要求,。危險作業(yè)罪是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中的輕罪,旨在通過降低入刑門檻,,發(fā)揮刑事制裁在安全生產(chǎn)治理中的震懾作用,。實踐證明,危險作業(yè)罪加入安全生產(chǎn)“犯罪圈”之后,,安全生產(chǎn)行政執(zhí)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更加密切,,移送起訴案件呈明顯增多之勢。與此同時,,由于罪名把握失當,,同類案件不同處理情形不同程度存在,其中不乏擴大打擊面的情形,。究其原因,,主要是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對該罪的構成要件存在爭議,包括犯罪主體的范圍,、“重大事故隱患”的界定,、“拒不執(zhí)行”如何判定,以及危險作業(yè)罪與重大責任事故罪,、危險物品肇事等此罪與彼罪的區(qū)分等,,對此,《解釋》在第2條至第5條予以了明確,為下步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提供了依據(jù)和指引,。
危險作業(yè)罪是具體危險犯,,構成本罪除了要實施《刑法》第134條之一明確列舉的三類危險作業(yè)行為,還須同時具備侵害結果要件,,即“具有發(fā)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現(xiàn)實危險”,。立法旨在通過構筑行為與侵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鏈條,嚴格限縮本罪的打擊范圍,?!艾F(xiàn)實危險”這一概念其實在安全生產(chǎn)領域并不陌生。早在2002年《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就曾出現(xiàn),,2014年《安全生產(chǎn)法》修改增加停止供電,、停止供應民爆物品強制措施,其適用前提之一就是要滿足“現(xiàn)實危險”要件,。但對于何謂“現(xiàn)實危險”,,理論界和實務部門一直未達成共識,使其以一種不明確的姿態(tài)進入到刑法條文中,。從辦案實踐看,,危險作業(yè)罪認定的難點主要集中在對“現(xiàn)實危險”的判定上。
“現(xiàn)實危險”意在表明危險發(fā)生的緊迫性與現(xiàn)實性,。由于事故往往是多因素耦合的結果,,因而這種緊迫性與現(xiàn)實性的判定,需要結合行業(yè)屬性,、行為對象,、現(xiàn)場環(huán)境,、違規(guī)行為的嚴重程度,,以及整改措施的有效性與及時性等因素綜合考量,有時還需要借助技術鑒定和專家意見,。很顯然,,這不是通過簡單定義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在《解釋》起草過程中,,圍繞“現(xiàn)實危險”的界定問題,,各方存在較大爭議,無論是“概況式”還是“列舉式”的解釋路徑,,均無法做到論證嚴密并邏輯自洽,,表明解釋的時機尚不成熟。在這一背景下,,通過辦理更多的真實案例以便進一步積累司法智慧,,顯然是一條較為穩(wěn)妥的路徑。我國雖不是判例法國家,但“兩高”發(fā)布的典型案例在指引地方司法實踐中發(fā)揮了重要指引作用,。本次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有一半涉及危險作業(yè)罪,,通過真實案情將抽象性的“現(xiàn)實危險”還原成易于理解掌握的辦案經(jīng)驗,一定程度彌補了“現(xiàn)實危險”概念難以界定的不足,,有助于司法裁判標準的統(tǒng)一,。
二是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一方面,《解釋》對嚴重違法行為實行從嚴的主基調,,以達到有效遏制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嚴重沖擊人民群眾安全感,,懲治此類犯罪必須嚴字當頭,突出打擊重點,。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寶馬礦業(yè)有限責任公司“12·3”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江蘇響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別重大爆炸事故、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中,,都有企業(yè)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yè),、拒不執(zhí)行重大隱患整改執(zhí)法指令以及安全中介機構弄虛作假的身影,成為安全生產(chǎn)治理中亟待解決的“頑疾”,。在總結事故教訓及司法經(jīng)驗基礎上,,《解釋》遵循《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原意,堅持“主犯”“幫兇”一起打,,通過釋明“強令”“拒不執(zhí)行”“虛假證明文件”等概念的具體含義,,將實踐中具有普遍性、突出性的嚴重違法行為及時納入刑法視野,。比如,,安全中介機構弄虛作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行為人具有明顯的主觀惡性,,包括故意偽造,、篡改數(shù)據(jù)以及隱瞞相關情況等幾種常見情形。從全方位規(guī)制造假者的角度出發(fā),,《解釋》對上述情形予以列舉明確,,解決了“虛假證明文件”認定難題。
另一方面,,《解釋》恪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謹慎擴大入罪范圍。《解釋》積極回應社會關注,,明確“虛假證明文件”承擔的是一種過錯責任,,將“生產(chǎn)經(jīng)營單位提供虛假材料、影響評價結論,,承擔安全評價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對評價結論與實際情況不符無主觀故意的”,,作為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出罪情形對待。同時,,明確了司法機關在辦理危險作業(yè)案件時,,應對根據(jù)犯罪情節(jié)和嚴重程度、行為人的悔改表現(xiàn)以及對量罰的態(tài)度實行區(qū)別對待的原則,?!皟筛摺蓖瑫r公布的趙某寬、趙某龍礦山開采危險作業(yè)不起訴案,,就體現(xiàn)了該寬則寬的精神,,有利于實現(xiàn)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
三是注重安全治理的整體性,、協(xié)同性,。安全治理是一種整體性、協(xié)同性的治理,,是立法,、執(zhí)法與司法的有機統(tǒng)一。
首先,,《解釋》注重刑事規(guī)范與行政規(guī)范的銜接,,促進責任體系均衡合理配置。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在性質上屬于行政犯罪,,行政違法性是刑事違法的前提,,二者的區(qū)別主要表現(xiàn)在量的差異,即所謂的“情節(jié)嚴重”,。危害生產(chǎn)安全犯罪的復雜性,,需要將司法理性與專業(yè)知識結合起來,,對罪名中出現(xiàn)的關鍵概念,、術語,比如危險作業(yè)罪中的“危險物品”“重大事故隱患”等,,交由行政規(guī)范進行專業(yè)判斷更為科學合理,,同時也避免了與現(xiàn)行行政規(guī)范的沖突,有利于均衡合理配置安全生產(chǎn)責任體系,。
其次,,《解釋》注重新舊司法解釋的銜接,確保刑事政策的統(tǒng)一性、連貫性,。一般認為,,危險作業(yè)罪是從重大責任事故罪(刑法第134條第1款)中進一步分離出來的一個罪名,二者之間是基本犯與結果加重犯的關系,。從罪狀描述看,,危險作業(yè)罪與重大責任事故趨于一致,區(qū)別主要在于一個是結果犯,,一個是危險犯,。《解釋》關于危險作業(yè)罪犯罪主體的界定,,與“兩高”2015年出臺的《關于辦理危害生產(chǎn)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22號)保持了銜接一致,。此外,提供虛假證明文件雖在《刑法》分則被歸類為“擾亂市場秩序罪”,,但安全生產(chǎn)中介機構犯罪卻具有經(jīng)濟犯罪與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雙重屬性,。《解釋》顯然考慮到上述因素,,在確定該罪入罪門檻“情節(jié)嚴重”的具體情形時,,參考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法發(fā)〔2010〕22號)規(guī)定的財產(chǎn)損失的標準(比如“違法所得數(shù)額10萬元以上的”),,并結合安全生產(chǎn)類犯罪的特點,,增加了導致人員重大傷亡的標準(比如“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安全事故的”),后者保持了與《關于辦理危害生產(chǎn)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22號)的銜接一致,。
再次,,《解釋》注重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銜接協(xié)作,持續(xù)推動溯源治理,。在安全生產(chǎn)治理結構中,,司法權與行政權存在既各司其職又互相配合的關系?!督忉尅冯m然是司法裁判規(guī)則,,但對行政機關執(zhí)法辦案特別是證據(jù)收集會產(chǎn)生實質影響。由于危險作業(yè)罪不要求造成重大事故后果,,對日常監(jiān)管執(zhí)法中發(fā)現(xiàn)的違法行為是不是需要移送,,行政執(zhí)法人員需要結合《意見》所確定的入罪標準予以判斷,避免以罰代刑,。此外,,先行政處罰還是先行移送,也是執(zhí)法人員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對此,,《解釋》第11條明確了“刑事優(yōu)于行政”的原則,,即被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需要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
總之,,靜態(tài)的《解釋》與動態(tài)的典型案例相互補充,,通過解釋原則性的法律條款,二者共同發(fā)揮規(guī)范裁判尺度,、統(tǒng)一法律適用標準的作用,。可以預見,,這種“司法解釋+典型案例”模式,,將會越來越多地運用于公共安全治理的場域,以滿足法治化發(fā)展的需要,。
- 一審:
- 二審:
- 三審: